

【赵白生,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主任、跨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、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会长、国际传记文学学会创始人、世界生态文化组织主席、世界文学学会会长。曾获北京大学唐立新奖教金优秀学者奖、德国弗赖堡大学高级学者奖、哈佛大学燕京学人奖、朱光潜美学与西方文学奖、赵萝蕤英美文学奖等。曾任英国开放大学研究员、法国里昂大学特邀教授、德国古腾堡大学客座教授、央视《朗读者》评点专家等。专著、编著、译著、合著有:Ecology and Life Writing、《东方作家传记文学研究》《哈佛读本》《传记文学理论》《元首传》等。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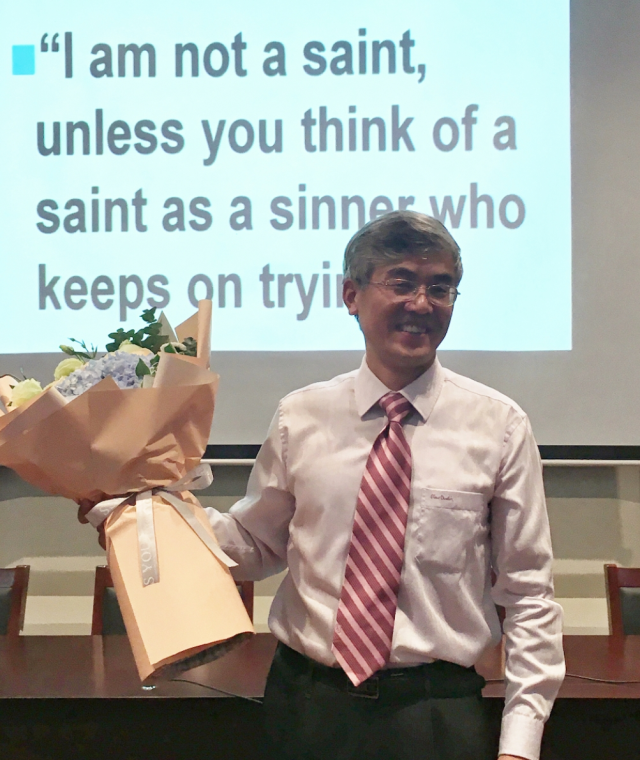
传学家,怎么当?
没头没脑,这样一问,真不好答。拆分一下,找出关键词,也许能理出头绪:传学、传学家、传记家。传学,简言之,乃深究传记文学的学问。有诗学、词学、曲学,而无传学,原因何在?难道仅仅因为没有一本《传学研究》的刊物吗?显然不是。如果一定要“开罪”于谁的话,传记家似乎有点责任。萧军、傅雷、张中行、杨绛、季羡林、雁翼……全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——自传家,但他们压根儿没有这样的身份觉悟。传记,讲究认可政治;自传,凸显身份美学,而传记家和自传家,对其身份的认可度,庶几于无。天大的讽刺,难道传学家就能辞其咎吗?
看来,有一件事,应该有人去做,那就是打造一个传学家和传记家的摇篮。传学家的身份认同、学术训练、专业素养、宏观视野,一条龙,全服务。
这样的摇篮,有吗?
1994年,对我来说,是个尴尬的年份。三十而立,立什么?没想好。1993年到北大,两眼一抹黑,既无人脉,也没学缘,单枪匹马,首先问问,能干什么?无人脉,因为我是外来户,刚刚从北科调入。没学缘,就是说,我的本科跟北大无缘分,硕士与北大也不沾边。如此背景,可偏偏有一颗不怎么安分的心。
庙大压死人。北大庙大,强手如林,人中龙凤,挤破园子。其结果,燕园虫,也就成了北大特产。一入燕园便当虫,于心不甘。心有不甘,就想起了出路问题。又正好赶上了令人尴尬的年龄。古人的话,就像头上的剑,逼着自己,当机立断。其实,当好燕园虫,并非易事。读学位——本硕博,十年苦心磨一剑;升职称——讲师副教授教授,廿载精力“投”纸背;胸中万卷吼,白了少年头。可是,这样按部就班,一眼望到头的路,偶尔也会觉得,无聊透顶。难怪现代人的日记有一大特征,满纸“无聊”。当时就想,应该干点什么,让自己的人生来点大激荡,多点小纪念。具体说,能立成什么,脑中无数,心里没底。但有一点并不模糊,想干点什么,既“不同凡响”,又“开天辟地”。
30岁的胆,有点不知天高地厚。
灌篮,虽然扣人心弦,可前面的两步起跑,往往必不可少。确切地说,创建国际传记文学学会(International Auto/Biography Association),是我跑完两步之后,才灌的篮。1994年,我创建“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”,立足全国;1998年,我创建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,扎根校内。扎根校内的“传记中心”,有了;立足全国的“中外传会”,也有了。有了这两大步,第三步,放眼全球,似乎瓜熟蒂落,题中应有之义,其实未必。1995年后,我被读学位捆绑住了,正在英文系执教,却在中文系读博,白天输出英文,夜晚输入中文,拳打脚踢,心虽不闲,倒也不累。可是,如果去草创一个国际组织,万事开头全是难,仅凭一己之力,起码得花三年时间。这样的时间成本,谁付得起?再说了,老套的学术评估系统,只注重科研成果、教学工作、行政服务三大块,根本不看是否为学术开辟新天地,创出新格局。像北大这样的大学,是不是也不能破格,在评估上别具一家?北大难道不是正在被“燕园虫”式的“学术工作者”所蚕蚀,而缺乏开风气之先的学术战略家,即龙头式的academic leader? 当“燕园虫”,还是“燕园龙”?抑或“龙虫并雕”,一如“了一”先生?所以,当我脑海里闪现成立国际传会的创意时,思前想后,并不心潮澎湃,相反,静得出奇。另外,我还有一块“心病”——出国镀金。学洋文者,而没留过洋,好比钱币,只有一面,终身只能一面示人,演绎纸上得来的“一面之词”。再说,《围城》里说了,出国,就像出痧子,非出不可。这个感觉,我有,但不是特别强烈。因为留学签证屡屡受挫,多了一种苍凉感——“出国未捷身先老”。苍凉感之外,还夹杂些焦虑感。原因不难找:当时流行张爱玲的话,出名要趁早。出国亦如出名,仿佛越早出国,其金越纯。
可是,为了成立“国际传会”,白手起家,创建一个传学家和传记家的国际大家庭,什么学位、什么出国,统统抛到了九霄云外。
这种豪情,现在想起来,相当危险。
事实上,就国内情况而言,1999年办一届传记文学的国际会议,困难重重。有些困难,似乎难以克服。加上我是“三无人员”——无官、无名、无背景,要把会办大,没门。办会,说到底,就是给自己挖坑。脚踏实地,面对现实,开会的三大难题:经费、人气、话题,我都有。更有甚者,我办会,还有额外的两大拦路虎:组织工作和翻译问题。这五大难题,搞得不好,犹如五马分尸,把会议的组织者给肢解了。
第一个头痛的是经费问题。当时办会,经费来源少得可怜,不像现在这个建设平台、那个重点项目,渠道一多,自然不愁无粮。1998年开始,我就扮演了一个新角色——乞丐大白,大有“逢人说款”之陋习,跑教育部,跑出版社,甚至跑过私营公司。我去那些地方,既不是为了跑官,也不是为了出书,而是为了跑会,“动机不纯”,目的纯粹,为了学术。当然,找的最多的地方,还是校内各单位:外语学院、社科部、校长办。每到一地,我见对方有空,就开始摆龙门阵,狂讲传记文学的“远大前程”,并不时插入隽永的传记故事,如“冒顿定律”“刘邦的黑色幽默”“为什么孔老二成了中国文化的男一号而天下第一的老子却屈居第二”,弄得好像满世界都知道,北大有个搞传记的,“素质教育的第一读本是传记文学”、“21世纪是传记文学的世纪”。见缝插针,苦口婆心之后,会议经费,有了落实。经费充足之后,我摇身一变,阔了起来,成了“慈善家”,资助特邀代表、资助传记作家、资助研究生代表、资助困难人员。北大、北师、贸大等校的研究生团队参会的费用,全免。没了后顾之忧,这些学生总是乐于为会议服务,或做翻译,或做导游。
每一场轰轰烈烈的背后,都有一个乞丐的影子。
学术大会,能否成功,全靠人气。人气无非凭“三势”:势众、势头、势力。国内办个会,邀请个一二百号人,往往不是问题。可是,我们的问题恰恰是,邀请不到一二百号人,甚至连像样的人,20人也邀请不到。因为在当时,中国专门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,北大、复旦、南大、北京师大、浙江师大、陕西师大、徐州师大等,加上社科院,算来算去,10人左右。偶尔写过传记研究文章的,也屈指可数。怎么办?好在,中国的名校,都有人在搞传记文学,这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又不能虚张人势,模仿诸葛亮,来个草船借箭,用箭头充人头。那样,银样蜡“箭头”,国外专家一来,非出国际玩笑不可。办法何在?就从传记中找灵感,学《史记》里的田单,用混成战队:长期研究传记文学的学者打前锋,青年教师和博士生等后备力量为中坚,传记家、批评家断其后。这样一来,中国团队的发言代表,也“浩浩荡荡”起来,有了50人左右,占了大会近“半壁江山”。这三股“势力”,后来构成了中国传坛的主力军,陆续出版传学著作,达百部之多。
“势头”,别解一下,乃造势之头,即梁启超在《李鸿章传》里所说的,造时势之英雄,而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。说白了,会议需要一个“会头”:形成众望所归、众星拱月之“势头”。这人,想来想去,非季羡林先生莫属。季先生,常常被称为各种“家”,数其荦荦大者,有语言学家、翻译家、散文家,甚至国学家。可是,我认为,他最重要的身份,应当是自传家。他的其他著作的影响力,不可能与其自传的渗透力相匹敌。季羡林先生的不朽,或许不是靠他的学术论文,也不尽靠他的散文译文,更不是靠他相当得意的《糖史》,而主要靠他的自传杰作:《牛棚杂忆》《留德十年》《清华园日记》。
看来,季先生是不二人选。
可是,季先生,怎么请?
虽然同在一个学院,也拜访过他,甚至还找他为别人的书签过名,可是,季先生年事已高,足不出户,越来越难请。如何打动他?得想个招。
登门拜访,交浅言深,显然不是最好的办法。打个电话,他无思想准备,话不投机,一两句,就打发了。琢磨来琢磨去,还是觉得,写信乃上上策。花了点心思,写了封信,说不定能够触动他的哪根神经。我有一点自信:看了信,季先生会相信我的“谬论”:21世纪,乃传记文学的世纪。信里,我估计会三句话不离本行,“季门”弄斧,大谈特谈北大的传记传统,从胡适之的《四十自述》和《胡适的日记》,经由冯至的《杜甫传》、邓广铭的《岳飞传》、张中行的《负暄琐话》,再到季羡林的《牛棚杂忆》、乐黛云的To the Storm, 一路下来,一个世纪,让人神往,也令人唏嘘。
接下来,就是等待。等待一点也不煎熬,因为忙着办会,千头万绪,没日没夜。掐指头一算,会期快到了,突然想起,还没有季先生的消息。难道说,没有消息,就是好消息?不过,还是不敢存此侥幸心理。开会前夕,突然收到季先生的信。他说,不能参会,但信中,他谈了不少他对传记文学的看法,也认可我的说法。得到季羡林先生的信,如获至宝。他虽然不能亲临会场,语“醒”四座。可是,有了他的墨宝,就感觉到,传记文学队伍有了把“尚方宝剑”,多了根“定海神针”。
会议的大贵人,还有两位,一直铭记至今。一位是北大副校长何芳川教授。北大人多,尤其食堂,熙熙攘攘,满眼望去,乌压压的一片聪明的头。可是,你一回想,真正记住的头,几乎没有。何校长不同,他是北大文科的领头人。其头,望一望,便难忘。他的头,像竹简,幽邃而爽睿,散发出一种古色古香的气息。听他讲话,你会感受到北大之大,一个大学所特有的大气象。因为那段时间,他在北大讲话,不论什么场合,都不忘提他的关键词——“大船”,北大要造“大船”。我听后暗暗思忖,北大好大,可大而无当,也是大,什么大,才算真正的大?也很好奇,想问问他。我们外语学院,就是他着力打造的第一艘大船。有人背后议论,什么大船,四个大系,合并成了一个小小的学院,明明是被裹了小脚。信乎?我一共请过他两次,有请必到。我原以为,领导都这么好请,后来才发现,并非如此。两次,都是为了传记文学。一次是1998年,成立北京大学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之时;还有一年之后,成立国际传记文学学会之日。我不知道,在他眼里,世界传记研究中心与国际传记文学学会,哪艘是大船?这两次,他都有一个共同特点:提前半小时到场,还亲自准备了发言。一位领导,日理万机,开会居然提前半小时到,时间安排,一如古人之余裕,树立典范。每次请他,他都不提让我准备发言稿,我也乐得偷懒。作为历史学家,他讲传记,对门对路,他讲完之后,下面的人拼命鼓掌,是为他的大船精神所感召,还是为他的口才所折服,我到现在也没有搞清楚。
胡家峦先生,属虎,望之俨然。可我跟他,天然亲,大概我了解虎性。我的父亲,也属虎。有次私下聊天,胡先生居然给我讲了某个同事的绝密八卦。像胡先生这样的学者,庄严得像云冈石窟里的一尊雕塑,他讲八卦,顿时触动了我的传记神经,让我感受到他身上的烟火气,一下子拉近了我跟他的距离。我请他去张家界参加传会,本想让他放松放松。没想到,他飞机上看书,宾馆里看书,开会时依然在看书。给人的印象,手不释卷,终身不倦。会场上,他看的是我们这届年会首次出版的会议文集《传记文学研究》。代表们的发言稿,赫然在册。这给胡先生一个“偏见”:小赵办事效率奇高,会没开,书已出。其实,这也是近水楼台,误打误中。因为我提前一年去长沙作演讲,用三寸之舌讲传记文学的无穷魅力,把湖南文艺出版社的人说得热血沸腾,准备大干一场。记得我的演讲之后,出版社当时有个北大毕业生,跟一位老编辑争辩,是赵白生口才好,还是钱理群会演讲。跟出版社合作办会,出本书,自然不在话下。
胡先生很少表扬人,对我也是如此。他表扬我的话,我是通过他的夫人杨老师知道的。杨老师告诉我,胡先生说,小赵从来不说别人的坏话。这个优点,让我听后,哭笑不得。我不说别人坏话,那是因为我见胡先生的机会很少,一年也见不上几面。而且我刚来北大没几年,也没有树敌的机会,进校直奔教室教书,离校飞奔回家备课。没办公室,无地可待,独来独往,乐得清净。这样,同事不认识几个,怎么说人坏话?我在传记方面的事,他支持最多。1994年成立中外传会,他力挺;1998年成立传记中心,他力挺;1999年成立国际传会,他力挺。一如既往,力挺如初。他是我的顶头上司,又是无条件支持先生,我自然得寸进尺,干劲十足。他的支持,让我觉得,人即使不需要翅膀,也能有飞起来的力量。
如虎添翼,不亦快哉。
有次传会,我邀请了社科院的李雅君博士。听完会后,她大发感慨:你们系主任胡老师、副校长何老师,头头脑脑全在,你一个年轻人,30多岁的毛头小伙,居然主持会议,还敢滔滔不绝,大放宏论。
归根到底,那代领导,像何校长、胡先生,就有这种魄力,放飞新进。
会议规模一旦确定,大会主题,最为要紧。办一个国际会议,核心议题的号召力,有时甚至能决定会议的成败。画龙点睛,会议主题,乃办会者的点睛之笔。选题三忌:老、窄、杂,我了然于心。我所面临的问题是,国内从来没有举办过传记文学的国际会议,这是首次。国外大型的传记文学国际会议,屈指数数,几乎没有。国内国际,没有经验,可资借镜。我当时自定了三个标准:选题追求前沿性,力戒老旧话题;会议的目的,就是为传记文学造势,议题太窄,没有人来,势从何起?议题博杂,是办会者的大忌,可对我来说,反而是大好事。传学者,杂科也。换言之,传记文学的最大特点,乃其交叉学科性,即大诗人叶芝所谓“所有知识乃传记”,或大文豪库切所言“一切作品皆自传”。不言而喻,传学家,乃杂家。传学家的这一基本素养,最好能体现在大会的主题中。除此之外,我最关心者,国际代表的兴奋点在哪?每年学术会议千千万,能让五大洲的国际代表一看主题,立马亢奋,自掏腰包,漂洋过海,来到北大,凭什么?
所以,这个主题,乃万有引力也。
这个难题,看似难于上青天。事实上,解决起来,并不费劲。因为那几年我的脑袋里,天天弹着传记文学这根弦,又撞上了世纪末,这个千年一遇的绝佳时机,还不干脆把“传记文学”跟“世纪末”的愁肠别绪嫁接起来?于是,大会主题,取名为“走向传记文学的世纪”,英文则为“Approaching the Auto/Biographical Turn”。明眼人一看,中文英文,并不吻合,因为没有直译,用意在于交互生辉,相得益彰。1999年办会,这个主题,十分应景,又非常前瞻。参会者来,理直气壮,“走向传记文学的世纪”,有心人甚至还会情不自禁地问一句:“21世纪,是传记文学的世纪吗?”
一种历史的使命感,不知不觉中,落到了会议代表的心坎里。
西方学者,看到这个题目,大有共鸣。欧美学术界,经过几次大的转向之后,如语言学转向、后现代转向、后殖民转向,转得有点晕头转向,特别是名目繁多的后学转向,越转越玄虚,成了文字游戏,全是漂浮的能指。世纪末,到底转向哪里?而世纪末的大转弯,在西方语汇里,本身含义就是一个转折点,Turn之谓也。千年之转,当然是大转折。这个节骨点上,我提出了“the Auto /Biographical Turn”(“传记文学转向”)。
传记文学转向,乃实学转向也。
这一转向,颇具新范式意义。传记文学的千年大计,于是乎,有了起始点。
“传记文学转向”的深远意义,当时并没有认识彻底。我只是觉得,自己有一股劲,想登高一呼。出乎我的意外,西方学术界的反响异常热烈。五大洲的学术圈,特别是传学界的代表人物和学术新秀,纷纷响应,跃跃“欲会”。参会的中国代表多人感慨,这届盛会,是他们见过的唯一一次国际会议,国人和老外,一半一半,平分秋色。国内办的某些所谓国际会议,往往特邀两三个老外,甚至请几个留学生充数,像清汤上漂浮的几滴油,点缀点缀,改变不了学术清汤的寡味。
会与会的差异,大矣。有的会,堪称学术史上的里程碑,而有的会则是过堂风。当然,相当多的会属于台阶会,为学术攀高,有所铺垫。里程碑会与过堂风会,有两个本质的区别。其一,这个会在该学科的学术谱系里会不会成为绕不开的原点,算不算发生学意义上的源头。其二,会上有没有发生里程碑性质的事件,如原创学说、重大发现、核心机构、学术宣言等。我办这个会时,源头意识,十分明确。会议资料的第一行,显豁地印着:
令我意想不到的是,加拿大名校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(UBC)的两位学者Susanna Egan和Gabriele Helms迅速接龙,北京会上就提出申请,第二年即承办第二届国际传记文学大会。我没有问,她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, 但有一点,不可否定,北大年会的高涨势头,有了后续效应,顺势而为,趁热打铁。第三届则由澳大利亚墨尔本La Trobe University的Richard Freadman教授主办。迄今为止,国际传会总部和五大洲分部举办年会,共达25届,其中总部大会的承办方为:中国香港中文大学(David Parker教授承办)、德国古腾堡大学(Alfred Hornung教授组织)、美国夏威夷大学(Craig Howes教授主持)、英国萨塞克斯大学(Margaretta Jolly博士与Sam Carroll合办)、澳洲国立大学(Paul Arthur, Rosanne Kennedy与Gillian Whitlock教授联手)、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(Julie Rak, Laurie McNeill, Eva Karpinski与Linda Warley教授共办)、塞浦路斯大学(Amy Prodromou与Stephanos Stephanides博士合作)等。20年来,已经形成惯例,传记大会年年有,双年为一届总会,单年四大洲同时举办四届洲际会议。参会人数,少则100多人,多达三四百人。传学之花,开遍世界,说“传记文学转向”,似无异议。可见,北大举办的第一届传记文学国际年会,成了名副其实的学术孵化器、学科发源地。传学家和传记家学术训练的最佳场所,莫过于参加这一届届年会。
中国代表,由我召集,参加了多届国际传会,其中8人赴德国、6人飞夏威夷、7人奔英国,所获国际资助,十分丰厚,个人费用几乎全免。饮水思源,他们没有忘记北大传会。因为传记文学,不少中国代表才第一次飞出国门,开眼看世界。
首届传会,乃里程碑。因为我创建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组织——国际传记文学学会(International Auto/Biography Association-IABA)。一届会议,如何才能有附加值?才能学术上青史留名?当时,我的脑海里一直盘旋着这个问题。最好的办法,可能就是创建一个国际学术组织。所以,邀请国际代表时,我特别留心,绝不能让个别国家的代表垄断会议。五大洲、五大洲,默默念叨,久而久之,成了我的三字经。我知道,美加代表,特别是美国代表,很容易邀请。但是,亚洲、拉美、阿拉伯地区,尤其是非洲的代表,举目四望,一个也不认识,怎么办?踏破铁鞋找线索,我给传学圈里能找到的所有知名学者,都发了传会通知,特别关照,广邀同好,共聚北京。这时,我还想了个大招。最重要的刊物,特别是专业杂志,如a/b:Auto/Biography Studies, Biography: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,都刊登会议海报。可要想产生海量影响,就不能只选择专业杂志。这时,我想到了PLMA 这类刊物,一旦露面,天下皆知。单独寄信与广登海报并举,其结果,欧美学者云涌,澳洲学者扎堆。有日本、韩国、以色列、印度的学者,更有非洲学者两名,这令我开心不已。安排大会的主题发言时,捉襟见肘感,烟消云散:我排出了五大洲的“豪华阵容”。特别是,能够听到来自非洲的声音,就已万幸。Judith Coullie博士的主题发言,“New Life Stories in the New South Africa”(“新南非的新传记”),满足了我们,至少是我,“别求新声于异邦”的心愿。这篇论文,也由郭英剑教授译为中文,登在《译文》上。说它是我国发表的最早的南非传记文学论文,不知可否?
最重要者,成立国际传记文学学会时,五大洲,“大满贯”。
其实,比这最重要者还要重要的,就是培育传学家的宏观视野,不能偏于一隅,东向而望,不见“南方巨子”。
全球南方,新的转型,难道从传学始?背离老“五四”的“中西模式”,开辟新路,树立学术研究的“南北模式”,可乎?
创建国际传记文学学会,无端地想起了辛词,“君王天下事”“可怜白发生”。我是细节主义者,这个组织,无数细节,没让我少费心思:由谁组成、性别比例、区域分布、如何运作、怎样活动,细细谋划,我心里没底,但唯一有数的是,我的这个创意,无论如何,一定落地,生在北大。面对众多国际代表,我们第一次见面,很不熟悉,个个年纪比我大,不少人甚至是父辈的年龄,我当然不能强推。因此,大会期间,我开了至少三次专门会,磨合磨合再磨合,力推这个组织,不但既当爹又当妈,还要当接生婆。首先,第一个会,也是最重要的会,开一个神仙会。请来各国神仙,畅所欲言,献言献策,这个国际传会怎么办。我怕冷场,就罗列了一个6人的发言名单,多半是传界重镇,一一点名,让其发言。然而,我发现,美国自传协会主席William L. Andrews不很积极,法国巴黎大学的传学巨头Philippe Lejeune并不热心,普利策传记奖得主Joan Doran Hedrick也很冷淡,典型的印度人德里大学的G.R.Taneja干脆放起了鸽子,无影无踪。有几个人,我原本不看好,反而热情无比。我就顺势邀请了这几位热心人,加上我选中的两三人,连续开了两次非正式的会:一次餐会、一次酒会。餐会特别丰盛,本希望他们任情饕餮,大饱口福,可他们似乎个个胃觉不振,无心恋食,仿佛置身于鸿门宴。谈来谈去,各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小九九。七嘴八舌之后,我只好综合大家的意见,这个组织,先搞起来,但实行非常规化,不设officers、不收会费、不设秘书处,只提供学术服务。说实在话,这跟我所设想的国际组织大相径庭。既然是国际组织,就得尊重民意。但我提出,这个国际组织,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工作团队,提议成立一个5人组委会,有德国的Alfred Hornung、美国的Thomas Smith、美国夏威夷的Craig Howes、英国的Margaretta Jolly和我。Craig Howes提出为国际传会做一个Listserve。新生事物,我那时听也没听说过,不断地问,怎么回事。这个学术服务群,已给国际传会招收了约1500名会员,每周源源不断地提供传记文学的各类信息。如果说刷存在感的话,这个Listserve,给国际传会所刷的存在感最强。我也提出,给学会做一个网站。筹备之后,网站建成,为学会安了一个永久的家。后来,学会网站由澳洲学者Paul Arthur接管。目前,这个网站由加拿大学者Julie Rak具体打理。
意外之喜,这个组织,却多子多福。国际传记文学学会(IABA)创建之后,各洲分部,犹如春笋,纷纷挂牌。首先,成立了国际传记文学学会- 欧洲分部,紧接着美洲分部落地,然后亚太分部诞生,最后非洲分部,也呱呱坠地。还有一个小可爱的组织,即IABA-SNS(国际传会-学生青椒部)。国际传会,已经不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,而是一片片森林,覆盖了世界五大洲。
传学家的身份认同感,来自哪里?
这个学会,便是家。
其实,传学家的身份认同感培养,也可以见贤思齐,从传学宗师身上承继学术基因。这届会议,中国传学大家与后起之秀,几乎悉数到场,有北京师范大学韩兆琦教授,上海复旦大学朱文华教授,浙江师范大学陈兰村教授、俞樟华教授,陕西师范大学张新科教授,徐州师范大学王成军博士,北京大学李战子博士、洛阳军外许德金博士等。传坛名家桑逢康、韩石山、胡辛、戴光中、宗道一,批评家王干、阎晶明等,纷纷撰文论传。中国学者们的发言,归纳一下,四个特点,相当显著:一、史的梳理,颇为系统:如“古代传记分类学”(俞樟华)、“刘知几的传记理论”(张新科)、“司马迁的传记观”(周旻)、“略议中国古代正史传记”(陈曦)等;二、域外传记,青睐有加:个案有“汤亭亭《女勇士》的文类”(姚君伟)、“作为文化边际人的赛珍珠”(郭英剑)、“莫洛亚的传记美学”(刘海峰)、“普拉斯的《书信》与《钟罩》分析”(黄健人)等;三、跨学科性,研究成风:政治、历史、宗教、语言学、心理学等纷纷介入传学研究,如“20世纪中国传记文学的历史位置”(陈兰村)、“古代中国的僧传:历史、宗教与文学”(王邦维)、“性别意识与迫害的政治”(李素苗)、“历史观念与文体意识”(王敦)、“认知模式与自传中的人际功能”(李战子)、“海明威传的语类分析”(王玲)、“新历史主义、精神分析学说与海明威传记”(邹溱)等;四、传论问题,小荷露角:“传记作者的主体性”(胡辛)、“自传故事的属性”(孙建秋)、“时间与传记文学叙事策略”(刘佳林)、“论自传事实”(赵白生)等。
国外代表的发言,个性突出,色彩斑斓,学术味道,浓如咖啡。只可惜,听的过程,十分享受,听完之后,笔记一丢,20年后,能记多少?
谈传学,离不开具体的人,而国际传会开得红火,也离不开两个人:
王敦敦厚,一如其名。听他说话,不紧不慢,从容深静,仿佛北京皇城根下的一棵古树,风雨飘摇,千年依旧。看到他,我首先想到的不是《晋书》里的王敦传,更不是吕思勉先生所定义的“敢行不义”“不肯下人”的王敦,而是普鲁塔克《名人传》里的费边。此王敦,非彼王敦也。他的办事风格,颇得费边真传,slow but steady,不急不躁,稳中求进。办会,最得力的人,就是一个“大管家”。王敦的这些品质,让我一眼就相中了他。“大管家”,非他莫属。这事,我跟他一说。他似乎想都没想,乐呵呵地就答应了。我心里犯嘀咕,当时他在央企上着班,怎么来?周一开会,三天会议,两天活动,整整一周,能行吗?但因为会议事多,东忙西赶,日夜不停,不久便忘了问他。21年过去了,他满世界跑了一圈回来后才向我透露这件小事:他向单位请了病假。理由吗?“得了重感冒”,大夏天,怎么会得重感冒?
传学家的座右铭是:VERITAS,唯真无它。病假的假,显然,触犯了“行规”。我不知道,是不是这个原因,他把这个秘密一直埋在心里,一埋就是21年。
这算不算国际传会的“原罪”?
不过,有了王敦,老外们欣喜若狂。他们的夜生活因此而打上了浓浓的中国特色。这些老外,不懂中文,出了会场,寸步难行。开会的惯例,“白天交流思想,晚上交流感情”。王敦带着他们,到北大周边的小馆子喝酒聊天,酒喝了多少,感情交流得如何,不得而知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,老外们喜欢上了这个“大管家”,纷纷送礼致意。送书的送书,送衣的送衣。当然,最让王敦感动的,是老外建议他出国留学,因为他们都以为,他是英文系的博士生,英文口语溜溜的。而事实上,王敦那时只拿了个北大的中文本科学位,心系远洋,却一纸合同,死死地困在央企,飞离不得。
这触到了王敦的痛点,令他失态,热泪纵横。
这次会议,我的外院同事,没有袖手旁观,共有10人提交论文,并参与发言。办会,确切地说,是一种“主场外交”。你把世界各国的学者邀请来,最大的忌讳,是唱“空城计”。你搭台,让别人来唱戏。为此,我事先做足了功课,早早地在英语系、西语系、东语系、俄语系、中文系、历史系等海报墙上,还有学校的各大广告栏里,贴上了会议海报。这些会议海报,好像绝大多数打了水漂。其实不然,这就像在荒漠里种树,不断浇水,特别是用心滴灌,小树才能成活,慢慢长大。传学这个学科,更是如此,最需要滴灌的人,持之以恒,终身为之。可是,现实问题也不得不考虑:北大老师,个个事情缠身,即使三头六臂,也忙不胜忙。找他们帮忙,无非两个方面:出智出力。这两个方面,我都需要。出智,就是让他们准备会议发言;出力,就是请他们来做现场的会议服务。在这两个方面,我的英语系同事傅国英老师,最为热情,至今难忘。她是急先锋,风风火火,一团火。你让她干十分的事,她会使出十二分的力。这样的拼命三郎,办会者最欣赏。会议期间,傅国英老师遇到会议代表,有问必答,忙前忙后,像一只欢腾的小鹿。无论是国内同道,还是国际客人,对北大的印象好,主要因为有傅国英这样的老师,投入到忘我的地步。后来,我听说,她上完课后,曾经跌倒在楼梯上。但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,不然,我至少会阻止她,让她做选择题,出智出力,两者只能选其一。除了忙会,她还赶写了会议的英文论文,深度参与。
两肋插刀,最佳写照。
这届传会,毛病在哪儿?20年后,再来探诊,不一定客观,但感触会更深。首先,国际传会的执行机构,过度西化。北京时期,问题并不明显,但已有病根。原因无它,参会的国际代表,主要为欧美学者。还有一段实情,传学研究,欧美国家,特别是英语国家,势头劲猛,实力雄厚。国际传会的决策机构即执委会,目前10名成员,9人为欧美澳成员,占绝大多数。没有拉美学者、没有非洲学者、没有阿拉伯学者、没有南亚学者、没有东南亚学者。西方学者,一方独大,尾大不掉,如何平衡,问题巨大。导致的后遗症是,最近的几届传记文学国际会议,大会的主题发言,为西方所独霸,慢慢地背离了北大传会的传统,即五大洲原则。我要纠偏,任重道远。
北京会议,没有出版会议文集,也是一大软肋。我的个人责任,不可推卸。会议一结束,我即负笈哈佛,忙于博士论文,一忙就是三年。记得在哈佛时,我的同学当着别人的面嘲笑我说:我们博士同班同学,我是博士,他还是个博士生。一字见血。忙了一场大会,拼死拼活,哪有时间,安安静静写论文。博士论文拖了后腿,这让我想起了胡适,像唐德刚先生所说,“摸鱼摸虾,误了庄稼”。太师爷的教训,一点也没有吸收。还算有点先见之明,我并没有承诺,要出会议文集。会议的部分论文,特别是主题发言,已译成中文,发表在《国外文学》《译文》等刊物上了。当然,我不爱出会议文集,有一个“借口”,说“别有用心”,也不为过。我组织会议,并不是没有出过论文集。张家界年会,我们以15天的闪电速度,出过一本411页的论文集《传记文学研究》。那本书,还请张中行先生题了签,一册在手,墨香四溢。我组织的各届年会,最为人诟病者,就是没出会议文集。这一点,传记家韩石山先生在理事会上刁难过我。我有我的“借口”,与其让泥沙俱下的论文集丢人现眼,还不如用自然淘汰法。好的论文,不愁出路。写得好的,发在核心期刊上,四面开花,影响大增。我们历届会议的论文,登在《北京大学学报》《文学评论》《外国文学评论》《国外文学》《外国文学》《跨文化对话》等核心期刊上的都有,还被名刊,如《新华文摘》等转载。这种方式,说不定比出本卖也卖不动送也送不掉的论文集更好。再说,我主编了《传记文学通讯》14卷,还有《传记年会手册》不少本。代表的发言摘要,尽收无遗。若想查一查传会档案,谁参加过传会,有哪些常识灼见,全部有案可查。
为而不有,功成不居;还是劳而无获,竹篮打水。清夜里,我扪心自问,问心有愧。
还有一个问题,属于学术的结构性问题。参加会议的代表,有三拨人:文史系出身者、外文系从业者、外国学者。这种三明治结构,本来是一种理想的结构,可以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。可是,实际上,交流起来,依然如风牛马。语言问题,倒在其次;知识结构,症结所在。语言层面,翻译可以解决,但知识结构的问题,翻译则解决不了。国际交流,往往只局限在三明治的两个层面。如何三个层面全覆盖,不仅是世纪难题,也是世界难题。文史系的同事,还懂些英文;外国学者对中文往往一窍不通。真正的交流,是双向的。我们西化,他们何时东化?关键是,依靠什么吸引力让他们东化?
国际传会的源头在中国,仅靠这一点,让人东化,行吗?
最后,言归正传,回到开头的问题:
传学家,怎么当?